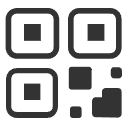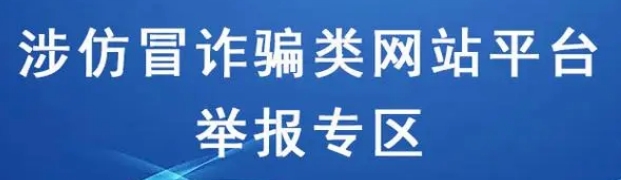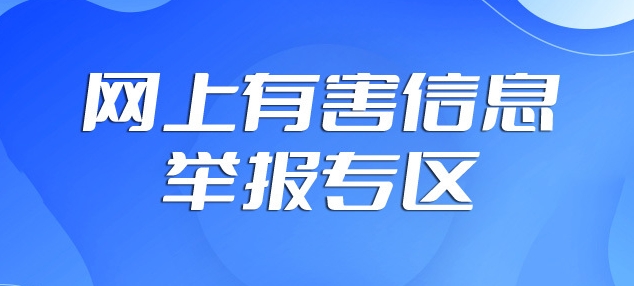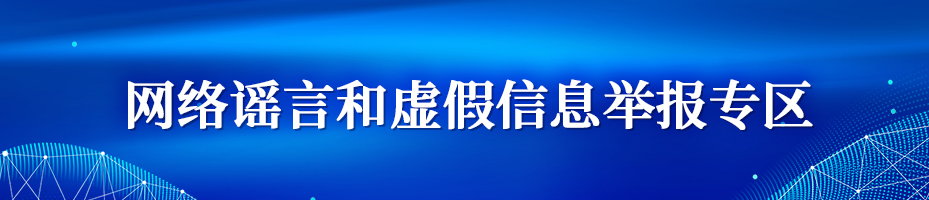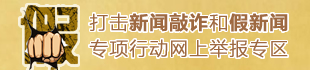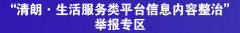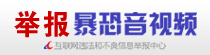小雪节令,没有落下雪影,却呼来一场大风,天刚蒙蒙亮就可着劲儿刮。风从西来,先刮跑了满天繁星。云往东去,天空变幻莫测:一排排如浪汹涌,一朵朵如莲盛放;不时和太阳玩玩捉迷藏,阳光一会儿热烈,一会儿阴郁,一会儿为阴云涂抹一圈亮色,一会儿舒展一袂五彩霞衣。躲在亮堂的玻璃窗内猫冬,心静着,风吹着,云动着,整个天空被我尽收眼底。
午时,万里无云,碧空如洗。我猜想那大片大块的云涛气浪定是不小心跌落进村外一眼望不到头的深壑中,亦或是一个筋斗就翻过了黄土塬,又被八缚岭的山风裹挟了去。阳光大大方方洒在床上,满满当当,明明艳艳。我钻进被窝,被窝被晒得暖暖的,氤氲着一丝儿甘醇,一丝儿土腥,一丝儿素净,一丝儿清宁。竟感到些许微醺,酣酣睡去。
一声响鼾戛然而止,醒了。嘴角不觉漾出笑意,准是自己又把自己“呼”醒的,说不准是风掀落墙头的半块老砖发出的动静。前两天还和朋友一起聊天,我说,越老越老得失了优雅,鼾声震耳欲聋。他说那是活得放松,肆意,满打满算也就剩一万来天,怎么着也得对自己好点。我哑声笑着说,有一万天那么久吗?我以为就今天和明天呢。努力把今天过好,努力把今晚睡好,明天也就成了今天。他连声说好好好,你真是活明白了,活在了当下。
活在当下,也乐在当下,就连漫天舒舒卷卷的云也能使我随心自在,虚度光阴。风嘶吼几声,云加厚几层。不多会儿云山叠嶂,欲雪无雪,欲晴不晴。正疑惑间,一大团乌云当头蔽日,天色陷入不合时辰的晦暗。
突然,这团庞然大物被生生撕开一个大洞,恰是洞开云天,祥光普照山川大地。那光愈是耀眼,那云愈是黑沉;那云愈是浓密,那光愈是炽热。后来刷到一个关于这番场景的视频,作者许是一个温婉的年轻女子,声音低柔却掷地有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炁能回归。”有置顶评论:天佑我中华!
智能科技,小小屏幕竟能使美美大同,人人大同。便有一种激越的情绪鼓舞着,试想以拙眼看出某些不寻常的风云况味。但终于风卷残云,太阳暖洋洋挂上了枣树枝杈,枝头风铃般摇曳的干枣们越发红润,争先恐后在空中舞着,摇着,荡着,划着一道又一道优美而莹亮的弧线。风似乎不乐意了,接连几个高抛,——噗,噗噗,枣子纷纷坠落。地上已经落了不少,三三俩俩簇拥着,也有独自躲进那处旮旯里的。这时候,我常是经不起诱惑,捡的时候欢喜,吃的时候喜欢,早把一天该吃多少的养生理论忘得一干二净。
捡回来的红枣里有不少已经被喜鹊或麻雀啄过,露着斑斑点点的印痕,裸出饱满丰腴的枣肉。我从来舍不得丢掉它们,而是将残损的部分仔细处理,洗净。取电陶炉,边煮茶,边烤枣,也烤梨。茶是甜红茶,煮好再放两颗烤焦的红枣,茶的甜香里又沁润了枣的醇香,茶汤红亮浓郁,任窗外西风烈烈,有这壶茶便暖了,香了,妥了。如果再吃一个烤梨,焦黑丑陋的梨皮内,是绵软多汁的梨肉,取小勺搲着吃,一口一口,甜甜蜜蜜。东北冻梨那叫一个“爽”,山西烤梨只一个暖,暖得祛除了冬的冷气和燥气。
儿子表示很不理解:妈妈,这被鸟啄的枣还能吃?我随手拿起一个来,在他眼前晃一晃:瞅好了,个顶个的大,个顶个的甜。知不知道为什么?儿子摇头。我冲他神秘地笑笑:鸟们鹊们都很智慧呢,它们巢的是老屋,栖的是老树,啄的是俊枣。儿子似懂非懂,又问:为什么总要在树上特意留一些枣呢?
那是因为啊——我故意卖个关子,《宝水》里寿数最长的九奶说,“这叫招喜,意头好。老理儿上叫留余。留余就是留福,留福就是积德。”(马肆)
【责任编辑 陈畅 实习生 翟培辰】